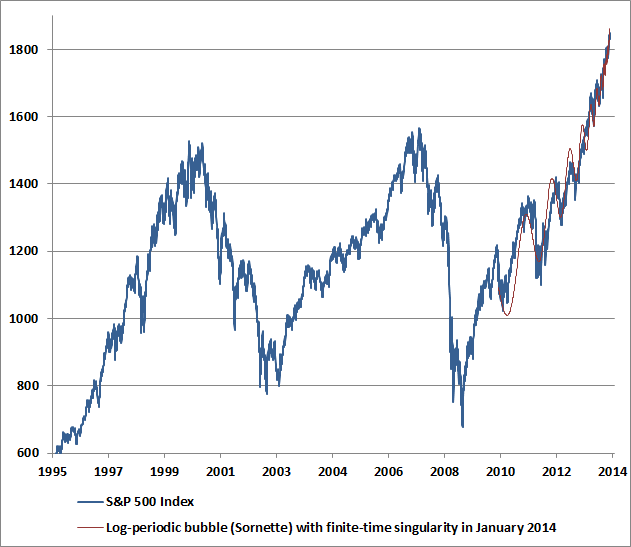2013年4月,我报名进入蓝翔技校,在计算机系网络技术专业学习了近二十天。
体验见这篇发表在时尚先生杂志上的文章。
另外,美容美发系的学习体验,我准备约另外一个哥们写,得等一段时间。
黑进蓝翔
我到达济南的那个中午,天色阴沉,乌云盖住整座城市。
来 接站的司机带我上了一辆溅着泥浆的黑色伊兰特轿车。开出济南西站不久,我们上了一条布满碎石与小坑的路。窗外灰尘弥漫,偶尔有渣土车轰隆驶过。司机走错了 几次路,我彻底失去了方向感,只记得路上尽是工地、汽配店、小饭馆、批发市场。不知过了多久,眼前出现一片灰色建筑群。车猛一拐弯驶进一座大院,我们到 了。
一个小伙子走过来,笑着跟我打招呼,帮我拿了行李。我匆匆打量周围几眼,四月的济南依然景色寥寥,巨大的广场后面蹲着一座方形的大楼,楼前是长长的阶梯,广场两侧栽种的小树没有几片叶子。这里的一切像极了某个县的县政府。
接待大厅里一片冷清,几个中年妇女在吃馒头。我觉得饿,要了一个馒头,就着白开水吃。大厅的一端是监控室,整面墙上安满了屏幕,看样子,摄像头布满了每个角落。
接 我的小伙子叫赵佳,我一吃完,他就说要带我到处转转。我点了根烟,跟着他在校园逛荡。从外面看,这里和内地县城的中学并无二致:外墙贴瓷砖的教学楼,宿舍 阳台上挂满衣服。偶尔能看到几个少年聚在一起抽烟,他们的工作服上布满了油污。赵佳跟我闲聊,一个肯定要被人反复问起的问题来了—
“怎么想来蓝翔了呢?”
2
今天,蓝翔技校已尽人皆知。早些年,它的出名是因为电视和广播上频繁直白的滚动广告,但让其声名远扬的是《纽约时报》的一则报道。2009年底,Google等几十家美国公司受到黑客的攻击。两个月后,《纽约时报》刊登了一则报道:
有 两所中国教育机构被追查到与一系列针对Google公司和其他几十家美国公司的在线攻击有关,其中一所还跟中国军方有密切关系……这两所中国学校是上海交 通大学和蓝翔技校……蓝翔,位于中国东部的山东省,是一所由军方支持建立的大型职业培训学校,为军方培养计算机科学人才。
这个消息令我吃惊。在我印象里,蓝翔技校是一个主要针对农村青年学习就业的地方,它培养的是厨师、汽修工人、挖掘机司机、美容美发师,不是黑客。这则消息就像民间科学家造出了载人航天器一样令人难以置信,更难以置信的是,它来自权威的、最具公信力的《纽约时报》。
我特地查阅了有关那次攻击其他的报道,几乎都来自美国媒体。综合起来,它们共同传递的是:有一批顶级黑客出现了,并且他们来自中国。
它 们认为这些黑客极度聪明,使用了十几种恶意代码和多层次加密,潜进受攻击的网络内部。更厉害的是,他们还巧妙地掩盖了自己的活动。就连美国网络安全公司 McAfee的副总裁Dmitri Alperovitchde 都说:“从未见过如此高水平的加密。在国防工业以外,从来没有商业公司遭到如此复杂的攻击。”
那些报道认定黑客和中国有关的一个理由是,攻击的目标往往极为明确─有利可图或者机密的知识产权。另外一个信息是,黑客试图通过六个台湾的网络地址来掩饰自己的身份,这是中国大陆黑客的惯常策略。
《纽约时报》的报道出来之后,蓝翔技校一夜成名。不过在国内,并没有多少人真正相信,人们更愿意在论坛和微博上以此调侃这所技校:黑客技术哪里强,中国山东找蓝翔。
一年过后,《华尔街日报》又刊发了一篇报道,再次提到蓝翔:
Google 公司说,中国黑客攻击了数百位知名人士的Gmail账户,受害者包括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及军方人员、亚洲地区官员、中国活动人士和新闻从业者 ⋯⋯Google说,它最近发现了上述攻击行动,源头疑为中国济南,并且是针对某些个人发动的⋯⋯专门研究中国的网络安全专家穆尔维农(James Mulvenon)说,曾经有人利用电子邮件向一家国防承包商发起定向攻击,蓝翔技校就是其中一个源头。
美国两大有影响力的报纸提及蓝翔, 蓝翔黑客的传闻开始变得严肃。我听到的传说也越来越多,有种说法是:蓝翔技校计算机系会传授黑客攻击的方法。还有听说它有一间全球最大的计算机机房,里面 有1000多台电脑。蓝翔深厚的军方背景也增加了传说的神秘感。在挖掘机和厨师铲的背后,在一堆潦草的初期班和速成班课表的背后,真潜伏着一批黑客的身影 吗?
我决定报个学习班,进入蓝翔。我带了几件换洗衣服,500元现金,一只诺基亚E5手机和一点感冒药,买了去济南的车票。
3
我 不可能告诉赵佳我到来的真正目的,我给自己编造的身份是一家灯具店的销售员,喜欢上网,知道蓝翔计算机培训很厉害,想来学点网络技术。我试探性地问赵佳蓝 翔是不是教黑客技术。赵佳说:“有一些技术很强的老师和学生,我有几个同学做木马盗游戏账号很厉害。”他的表情看似真诚,但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跟我一样, 提前就编好了一套蒙蔽别人的说辞。
走出校门,我们沿着马路走向斜对面的一个大院里,那是我未来上课和生活的地方。我当时并不知道,在马路上穿行往返的这十几分钟竟是我在蓝翔技校上课期间唯一走出校园的时候。在那之后的二十天里,我失去了自由。
蓝 翔技校在济南西郊的天桥区,离黄河不远。它像一个独立的小王国,三个紧挨着的大院呈7字形分布,每个院子都被铁栅栏和水沟围起来,彼此之间靠铁制的过街天 桥相连。学校西面和北面有两片荒地,南面是个新开发的住宅小区。大多数时候,校外经过的车辆和行人都寥寥无几。唯一的公交车站牌孤零零地站在路边,人行道 树的叶子上沾满了灰尘。
“平时能出校门吗?”我问赵佳。
“不让,周末出去也得请假。翻墙被抓到要罚钱的,不要冒险。”
这么警惕,真的隐藏着什么秘密吗?回到接待中心,我立刻交了一万块,报了一个网络技术班——这是我预想中最接近黑客技术的专业。收费员扔给我三张收据、一本字迹模糊的红皮学员证和一张塑料饭卡。我正式成了蓝翔的一员。我向收费员索要发票,她说,这儿从不开发票。
赵佳将我带到领取被褥的库房就消失了。一名穿黑色夹克和运动裤的年轻男子走进来,“提着东西,跟我去宿舍。”他叫陈伟忠,今年25岁,是我的班主任。实际上,他比不少学生还年轻。
走进宿舍楼,温度骤降,厕所飘来的臭气充斥楼道。放好行李,我跟着陈伟忠去了计算机房,那个号称全世界最大的、有着1000多台电脑的机房,那场面一下就把我镇住了。
机房里坐着20多个学生。他们正在上实习课。一群人围住陈伟忠,把假条递给他,希望能够到校外去,理由有重病就医、办银行卡、补办临时身份证。陈伟忠很严肃地宣读了最新的通知,校方实行了更加严格的制度,学生处停止在假条上戳章。批假一次,副校长要被扣去200元。
我找了一张空椅子坐下。
“新来的?”
“嗯。”
“唉,居然有人自己送上门来。这儿连假都不给请,整天被关着。”
蓝翔技校引以为豪的准军事化管理方法之一,就是严禁学生随意走出校门。他们说这样做学生会将更多时间投入到技术钻研中。这是个荒唐的理由,怎么没见北大、清华把学生关起来。封闭学校的另一个效果是,外人很难进入这里,一窥究竟。
4
我来之前预想过可能的遭遇。比如他们只给初入学校的人讲些粗浅的网络知识,作为掩护;比如某个老师认定我是可造之才后,也许可以招募我加入神秘团队。
第 一堂,我学的是如何用Word制作个人简历。同学说,前一天讲的是如何插入和制作表格。我颇为疑惑,这是我报的网络技术班吗,为什么在教Word?上课时 我发现,课堂上还有好多报名其他专业的学生,商务办公、网络技术、平面设计和环境艺术的,他们都在学Word。陈伟忠讲课基本上是照本宣科:“先插入分隔 符,分节符里选下一页,再添加页眉页脚⋯⋯”讲完Word部分,他还会普及一下平面设计基础知识。课堂里大约只有一半的学生会认真听,其他人要么打瞌睡, 要么玩手机。
连续几天都是如此。学Word对我真是种折磨,但我依然装作认真,告诉自己要有耐心。黑客也需要个对外身份,没有哪个人会在额头上贴着黑客两个字,也没有学校敢一上来就教黑客作战指南。
或 许是新老师的缘故,陈伟忠对课堂纪律要求不严。一次上课,学生没有在座位上而是围在老师身边听课, 还有人在教室里走动。突然,我们背后不知什么地方的喇叭发出一声呵斥:你们是哪个班的,把班级名称写在黑板上。陈伟忠怔住了,随后走到讲台上,写下“商务 办公”四个大字。我这时才想起来,教室后面有个摄像头。后面那双眼睛的主人估计在接待中心里喝着茶,他无时无刻不在盯着所有人。
在学校呆了 一段时间,我才打听清楚,我报名的网络技术班学制八个月。教学安排是,头两个月学办公软件,中间三个月学平面设计,最后学网页制作的相关知识。如果这样, 我很难在短期内有收获。我想了个办法,去找副系主任尹国辉,要求旁听高级技工班课程,或者转班直接学习网络技术。他拒绝了我:“学校没有这个先例,你想学 后面的内容可以自学嘛,内容咱们服务器里有。”
我想利用这个机会,探探他的口风:“外面都说咱们学校计算机系很厉害,有黑客,真的吗?”
“我持保留意见,我不能跟你说,嘿嘿。学校没必要做这样的广告,这是要杀头的广告。”
我 还想到一个人─计算机系主任邵红伟,他是《纽约时报》那篇报道中采访到的一位蓝翔“教授”。在一次闲聊中,我和同学提起这个人,同学告诉我,邵红伟说蓝翔 技校攻击Google公司是被人恶意陷害。邵还半开玩笑,自己因为这件事一整年都在应付采访,连美国也不敢去,怕被抓起来。
尽管蓝翔技校一 直否认与黑客攻击有任何关联,但学校里谈论黑客并不是禁忌,某种程度上,黑客事件成了一个理想的广告。美发专业负责招生的老师曾说,蓝翔技校计算机系实力 雄厚,黑客能攻击美国。美发系学生刘复生就问过我,黑客到底长什么样?我语带嘲讽,但相当真诚地回答:“我也想知道!”
5
我最经常去的地方是机房,我认为那是“黑客”最有可能现身的地方。
蓝 翔有两个巨大的计算机机房,在一栋毫不起眼的五层楼里,楼下是数控机床车间、汽修车间和电工电子模拟室。我每天上8节课,实习课就在五楼机房。2006 年,那个机房因为有1135人同时操作电脑,进入一项吉尼斯世界纪录。我去的时候只有893台显示器,超过一半的机器多年未用,被灰尘覆盖着,远望过去像 一片“计算机的坟场”。有的键盘飘荡在半空中,有的主机已经不知所踪。“坟场”的角落里有一堆拆散的零件,就像动物的骨架,那是计算机维修班的学生实习用 的。
我们用的电脑是方正文祥,一款老式计算机,内存只有512MB,CPU是英特尔Celeron(R),17寸显示器。开机后屏幕上显示 机房守则,第四条是这样的:修改IP地址、安装防火墙、破解客户端及系统设置等影响网络运行的行为将重罚。其他条款是保持卫生,穿鞋套进机房,不要吃东 西。
机房由一个叫老任的老头管理,外号“长老”,60多岁,头发有些白,总是面无表情。当发现有人在机房吃东西,或者带着食物进入机房,他就会发火,用极其严厉的语气加上几个简单的词汇让人感到压力—出去吃,不许吃!下楼去!下去!
机房最让人捉摸不透的规定是─禁止学生自带电脑。两名数控专业的学生将笔记本电脑带到机房使用,被老任发现,他奔过去,用手指着他们,大吼:出去!不准用笔记本。两名学生刚想辩解,老任已经冲过去强行把电脑合上了。
蓝 翔的另外一个机房,在四楼,两个机房最大的区别是,五楼不能上网,但四楼可以。它和实习的机房一样大,更像一所巨大的网吧:红色高背软座椅,金河田机 箱,AOC和三星牌21寸显示屏,叫不出牌子的键盘、鼠标和耳麦。电脑的CPU是AMD Athlon II X2 631,内存有 3318MB。在这里上网,每个小时的费用是3元,上机前先刷饭卡。
四楼“网吧”有一间小卖部,卖饮料、方便面、火腿肠和雪糕,我通常会在 这里先买一瓶健力宝再去找机器。小卖部外面坐着吃方便面的人,他们大多是下课后不吃晚饭就过来上网。我们喜欢穿过整个大厅,选最里面并且挨着窗户的一排机 器,这里凉快,不会有人在背后走来走去,没人能窥探我在做什么。开机后蹦出游戏大厅的窗口,可以选择玩单机游戏或网络游戏。单机游戏里有实况足球8、红色 警戒2、重返德军总部、CS这些古董级游戏,几乎没有人会去玩它们。这里上网的人基本上只玩《地下城与勇士》、《英雄联盟》和《穿越火线》这三个游戏。
我常常观察旁边的人,妄图找到“黑客”踪影,但我发现女生们要不在忙着看《甄嬛传》,要不就在购物,不停在蘑菇街、美丽说和淘宝几个网站之间切换,男生们几乎全在玩游戏,偶尔有人看《少年Pi的奇幻漂流》。
那个大网吧会营业到凌晨2点,周六通宵开放,我一般在晚上8点半左右离开。我不止一次想过这样的场景:在弥漫着方便面味道的四楼机房,黑客点击鼠标,万里之外大洋彼岸乱作一团。但每次我扫视这个巨大的网吧,实在想象不出,这些人里谁会是黑客。
在 蓝翔呆了十天,我萌生出另外一个假想:巨大的机房只是给一般学生用的,会不会还有一个秘密机房供更高级、也更隐蔽的人使用?我逃了课,在校园中游荡,把几 乎每栋楼都勘察一遍。在那栋像县政府办公室的楼里,我发现了一个隐秘之所。那栋楼的一层到五层是汽修和烹调专业的教室,从第六层开始已经没有人出入的踪 迹,地板、门窗上都覆盖着厚厚一层灰尘,从墙上脱落的瓷砖碎片散落在过道里,卫生间的门破了,水流到走廊上。通往第七层的所有楼梯都被堵住,障碍物上贴着 告示:严禁上楼,违者开除。
我没有理会警告,翻过障碍物,继续上楼。我像一个幽灵游荡在死寂的大楼里,从东走到西,上楼,再从西走到东。每 个教室都被锁住,里面是空的,只是脱落的瓷砖碎片越来越多,地面的灰尘越来越厚。阳光从走廊最西端的窗口照进来,将我的影子拉得很长。终于到了楼顶天台, 被玻璃顶棚盖着,像一个种蔬菜的大棚,别无他物。真是野合的好地方—当时我唯一的念头就是它。
6
如果不上网,晚饭后我和同屋的王鹏飞就去散步,每人拿一瓶崂山啤酒,边走边喝。
王 鹏飞不满18岁,脸上长着青春痘,头发烫成波浪型。初中毕业后,王鹏飞没有考上高中,在家玩了一年多。当包工头的父亲数落他不务正业,混吃等死,他意识到 自己正成为家中的耻辱。过完春节,王鹏飞从岳阳坐了19个小时的硬座来到济南,在蓝翔技校学习环境艺术设计。他的职业方向非常明确,像他表哥一样成为室内 设计师,“拿每个月1万多的工资”。
王鹏飞是我那个班上的同学中还算是年轻、上进的,他是唯一我能经常聊聊天的人。我在的班有20多个学 生,他们中有退伍军人、搬运工、保安、污水处理厂工人、被开除的大学生、退学高中生、群众演员。最大的41岁,最小的15岁。他们大多来自小城镇或农村, 希望通过计算机培训获得一份收入更高、相对体面的工作,没有一个人说自己想成为一名黑客。年龄最大的孙栋曾是一名保安队长,在北京大钟寺地区的写字楼上 班,他报名的是3个月学制的商务办公班,打算学完之后回北京找一家物业公司继续上班。
对于教学进度,王鹏飞非常不满:“我交了1万来学设 计,总共就10个月,现在还要拿两个月来学Word,难道以后要我用Word去给客户搞设计吗?你也交了9000多学费学网络技术,现在每天学Word, 不觉得很亏吗?”但不久,他就停止抱怨,用手机上的京东客户端买来PS教材和U盘,准备自学。
我和王鹏飞聊起过黑客。他认为,黑客很可能是 一场为了吸引眼球的炒作,他对此不感兴趣。他觉得校方禁止学生走出校园,不是要掩盖什么秘密,是为了让学生多在校园里消费,尽量榨出学生身上的钱。王鹏飞 来这里40天,已经花了5000元。校园里购物不能使用现金,必须把钱先充进饭卡。为避免私下的现金交易,校方规定,学生举报店主收现金被证实后,能获得 500元奖励。
学校里伙食不佳,做菜放的食材是头天夜宵没有用完的,米粒干而硬。虽不至于难以下咽,但毁掉人的心情却绝不是夸张。为了出去 吃一顿好的,学生们总是想尽各种方式,从翻墙到跟老师搞好关系。除了我,同学中还有一个人不那么干。那人叫李云山,他穿好成套的西服,皮鞋打好油,背起商 务挎包,手拿iphone,装成老师大摇大摆地走出去。
我注意到李云山的时候,他正坐在床上向其他学生演讲,主题是屌丝如何在一家公司发迹。讲起如何跟领导搞好关系、如何吃定客户时,虽说他刚20岁,却仿佛一个职场的老油条。
李 云山很健谈,几乎可以参与任何话题。从中日关系到去哪里修好笔记本电脑,从国家领导动态到教人如何与姑娘拍拖。我让他推荐一部手机,他先讲三星因为代工 iPhone偷师苹果技术,并超越苹果。然后继续滔滔不绝地说柔性屏幕手机、谷歌眼镜乃至iWatch。他甚至知道苹果取消了给富士康的订单将它们迁回本 土制造。
王鹏飞对李云山的“博学”很不屑。“他就知道吹牛,在试学处上课时比老师还懂,结果挨了打。还说家里有辆本田,鬼才信,有本田还来这里?”
在 试学处,李云山总是能回答出关于IT的各类问题,而其他学生还是一脸茫然。李云山自称曾在一家信息工程公司任职,负责电脑安装、维修以及大型局域网架设, 对IT领域有所了解。老师不这么认为,他们怀疑他是竞争对手派来争夺生源的卧底。据说李云山被24小时监视,他像瘟疫一样被人躲避着。试学的最后一天,李 云山被单独锁在办公室里,邵红伟和一名田姓副校长扇他耳光。他们收走了他的身份证、驾照,在ATM机上输错3次密码锁掉他的银行卡,要他交学费来证明自己 不是卧底。无奈之下,李云山只得同意交3个月学制的商务办公专业的学费。交完钱,一切变得好商量。尹国辉甚至建议他读2年制高级技工班,并许诺他“毕业后 留校当老师”。
在中国,总共有近2900所技校,民办职业教育培训机构互相之间竞争激烈,派人抢夺生源,乃至偷师对方课程都曾经发生过;雇 佣“水军”,在网上发帖攻击对方更是家常便饭。有意思的是,蓝翔技校极力否认培养黑客,但它的竞争对手新华电脑学校却将黑客技能培训写在《职业培养手册》 上,网站开发高级工程师专业的学习内容就包括“网站安全漏洞检测与黑客入侵”。
7
十几天过去了,每天都是机械地重复头一天。至于寻找黑客,没有任何突破。我做过一个梦:我第一天到蓝翔,系主任在办公室一一给我介绍计算机系的老师,他们很客气地站起来跟我握手。我看到每张办公桌上都放着一份《纽约时报》⋯⋯
一 次偶然的交谈让事情有了进展。有天上机实习,坐了一个钟头后,我准备出去抽烟,站着扫视一圈,想拉个同伙。老任坐在一台电脑前,噼里啪啦地敲着键盘。我走 到他身后,好奇地盯着屏幕,他正在往黑色的对话框里输入代码,我问他在做什么。老任是球迷,我们聊过几次中超联赛。他没回头,慢悠悠地说:“我在修机 子。”
“真看不出您老还有这手艺。”
“是啊,都搞了快四十年了。”
“四十年前咱们国家有电脑吗?”
“外面没有,部队里有。那不是电脑,叫大型机。”
“您以前在部队搞计算机?”
“对。”
“那您具体做什么?”
“软件开发。”
“是部队请您去帮忙,还是……”
“我就在部队里。”
“你是军官?什么军衔?”
“上校。”
老任还在摆弄那台电脑,周围还有很多人,我没有继续发问,独自下去抽了根烟。到蓝翔之前,我就知道这个学校和部队有关系,只是没想到,连一个打扫卫生的老头都有这么强的技术背景。这是一个好消息。
第 二天,我趁午休时去机房找老任,他正在玩连连看。我还是用现在学不到东西作借口引入话题。“我在网上看到蓝翔技校攻击过美国公司,觉得这里能学到真东西。 但怎么来了光学Word呢。”老任说:“攻击美国那是他妈的美国挑事儿,和咱们没关系。咱们哪能搞这玩意啊,咱这以前都没外网,4楼还是去年刚弄的,攻什 么击啊。”
老任回忆说,蓝翔技校涉及“黑客攻击”的新闻是假期时出来的,学校几乎没人,也没办法查出为什么蓝翔会跟这档子事扯上关系。我想 知道更多的细节,老任并没讲,而是给我讲了一通黑客攻击的原理。他说,理论上任何一台连上网的电脑都可以进行黑客攻击。但现在的攻击方法和以前不一样,很 难查出攻击者是谁,因为黑客无时不刻都在“养鸡”,也就是秘密地控制他人计算机发动攻击。“如果别人利用我们的服务器做成攻击机,这就没办法了。现在没有 人敢直接攻击,都是通过好几道弯,转来转去。没那么笨的人,让人逮住。”
从现在公开的调查看,原理确实如此。攻击Google的黑客进入系 统后,他们将数据发送给位于美国伊利诺依州和得克萨斯州以及中国台湾的指挥控制服务器。台湾内政部警政署科技犯罪防制中心主任李相臣曾出来辟谣,说台湾公 司可能都是受害者。《华尔街日报》文章里提到,黑客试图通过台湾的网络地址来掩饰自己的身份,说那是中国大陆黑客的惯常策略。但就像老任讲的,黑客隐藏自 己的手段这么高明,谁又能认定蓝翔是受害者,而不是最终点的攻击发动地?
我后来曾向国内一家网络安全公司的创始人赵伟咨询过蓝翔成为肉鸡的 可能性。赵伟在网络安全领域小有名声,甚至被怀疑过是那次攻击行动的参与者之一。赵伟说,老任讲的这种情况是可能的,“养鸡是黑客的日常工作,也是攻击的 基础,攻击必须先找跳板。不光是蓝翔,国内很多大公司网络安全防护意识和手段都很原始。黑客首先就找那些老弱病残下手。”
即便这些都说得 通,但老任的身份还是让人好奇。我问起他的过去,老任对这些倒没什么忌讳。八十年代,蓝翔技校的创始人荣兰祥和济南军区55151部队合作办技术培训学 校,校址就在部队大院里,老任那时正在这个部队服役,认识了荣兰祥。之后,老任转业到地方工作,退休后就被返聘蓝翔技校,至今已有8年了。
老任说他挺喜欢机房的工作,虽然杂事多,但不像教课那样累,况且教课老师的待遇并不高。他觉得年轻人不见得能干得好机房这个看似简单的清洁、维修和防盗工作。
我 了解的信息和老任说的一样,蓝翔曾经跟部队合作办学,在部队经商的浪潮中被“收编”:部队提供更大的办学场地、部队也介入学校经营管理,荣兰祥自己也成为 部队的职工。1998年,中国军队被中央军委命令退出商业领域,技校重新回到了荣兰祥手中,并在天桥区建了新校舍。脱离部队后,蓝翔技校还“带着部队的一 些家属和职工”。
直到现在,蓝翔技校也基于专业特长,跟部队进行一些培训项目的合作,像电工、汽修。每年有不同专业的高级技工班毕业生入伍,成为技术士官。荣兰祥很乐意讲述他和部队之间的良好合作关系,地方企业拥军是被政府所鼓励的。
8
在 蓝翔的二十几天里,我一直想接近陈伟忠,向他打探些情况,我提出去他住处,被他拒绝了。我怀疑蓝翔的老师中可能有人会是黑客。对于陈伟忠的冷淡,我开始以 为是他对我抱有警惕之心,后来才听同学说,陈伟忠这样级别较低的老师,连间自己的房间都没有,几个老师住一个宿舍,根本没什么独立的空间。
一天中午,我回到宿舍,有点意外地看见陈伟忠坐在床边和一个学生下象棋。我凑过去,看他们下完那盘棋,和陈伟忠聊了起来。他宿舍的下水道坏了,为了躲避臭味,午饭后就到我们这儿来了。
他问我原来是干什么的,我告诉他自己是摆糖水摊的,一直对计算机感兴趣,被蓝翔技校有黑客的传闻吸引,以为网络技术会教黑客攻击手段。
“我也不知道是真是假。就我这个级别,我估计没有机会了解到那些事情。网络技术是程甲老师教。程老师是咱系老师中工资最高的,比系主任工资都高。” 陈伟忠说。
程甲为什么能拿全系最高的薪水,他会是黑客吗?我想多打听一些程甲的信息,但陈伟忠说他仅见过程甲几面,没有太多交流。他只知道程甲是计算机系唯一的重点大学毕业的老师,技术很好,但是平时很少授课,专门管理学校的网络中心。
我 后来联系上了程甲,那是我从蓝翔逃出去之后的事儿。我也想等到程甲给我讲课的那一天,但不可能,那还需要6个月。我向赵佳要了程甲的手机号码,拨通了他的 电话,借口是请教专业课程以及就业出路。电话那端,有他孩子的吵闹声。他操着山东口音的普通话,给我介绍网络技术专业以后可能会讲到的一些内容,和我以后 可能的出路。
他告诉我,学生毕业后从事技术工作的很少,能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找到工作的也很少。“咱们的学生还做不了软件开发,但做实施是没问题的。”
我 又问起他的工资。全系首屈一指的薪资,其实才不到6000元。程甲从山东大学计算机系毕业后做过程序员,2008年到蓝翔技校。他也想过要离开蓝翔,北京 一家开发医疗软件的公司曾经高价挖过他。但考虑到家庭,他暂时留了下来。“软件行业总出差,家里有个孩子,走不开。”他说。
我向他表达对黑客的好奇。他听完,笑了,很干脆地说:“黑客违法,学校不教。咱们这确实没有黑客,谷歌攻击也不是咱们做的,咱们也没有那么高水平的人。”
我追问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他给我讲述了另一个版本的蓝翔技校黑客风波。
2010年2月,通过网络关键词监测系统,蓝翔技校发现自己成为爆炸性新闻的主角之一。震惊之余,立即排查,发现4楼机房有一批计算机中毒—具体何时中毒不得而知—可能被人作为发动网络攻击的中转站。从程甲的说法来看,这并不是像老任描述的那样,“机房以前没有外网”。
“有些机器变成肉鸡了,就是能够被别人随便操控的机器。他们通过咱们的计算机攻击美国的服务器,美国那边就以为是咱们攻击的。闯入别人的电脑都显示一个IP地址,都来源于蓝翔技校,但具体是哪一台就没办法区分了。”
从 谷歌的声明来看,攻击者的方法是,通过“钓鱼邮件”将Gmail用户引向诈骗网站,诱骗他们透露邮箱的用户名和密码,从而得以阅读并转发受害者的电子邮 件。在这种情况下,通过追查原始攻击源来证明清白是不现实的,即使查出前一级发动攻击计算机的IP,它们仍然有可能是一批“肉鸡”。蓝翔技校迅速切断了与 互联网连接的总接口,断网持续了将近一个月。当时怀疑中毒的一批电脑目前已经更换,无迹可寻—当时的电脑也是方正文祥。
我向程甲问起,《纽约时报》的文章提到蓝翔有个乌克兰教授,可能是黑客。程甲在电话里否认了这点:“哪有外国老师,全他妈是中国人。”
9
第 二十天,我全部的所思所想是如何逃出去,尽快结束这个玩笑—花1万块钱,用物理行为去核实一个技术问题。我曾精心策划过两次请假:我到校半个月没有洗过 澡,要求去学校对面澡堂洗浴,学校的浴室近一年没有开放过;老家新农村建设,房屋改造,需要我本人签字,但都没有被批准。在一次集体劳动时,我得到通知, 学校决定加强出入管理,不允许任何学生出去,但没有公布这样做的原因。我知道以请假回家为理由,彻底消失,是不可能了。
只能寻找所有可能突然出现的人间蒸发机会。
第 二天,气温罕见地蹿升了10度,午后阳光刺眼,大多数学生正在午休。我原本准备打一杯开水,再去机房找老任聊聊。去的路上,我看到校门开了一道小缝儿,没 有任何犹豫,我冲向那道门缝儿─马上离开!我加快脚步径直往外走,两个门卫的大声质问被甩在耳后。出了门,我沿马路一直向南走,跳上一辆正在驶过的三轮摩 托车,坐在挡板上。我在蓝翔技校的学习生涯正式结束。
来源:http://www.zhihu.com/question/21443217
![]()
![]()